题记:自2020年冬处 女作发表,至乙巳年百篇成帙。写作让我这个退休之人重获度量世界的尺——俯身捡拾市井烟火,以文字焐热平凡日常。锅碗瓢盆、街谈巷议皆成文章,写作不再是消遣,而是安顿灵魂的舟楫。这百篇文字既是对流逝光阴的深情回望,亦是继续前行的号角。笔锋如针,缝岁月为衣,让我始终坐在生活的前排,做自己人生的忠实录者。

2020年11月27日,我的第一篇散文《且将他乡作故乡》在《中国作家网》悄然登场。那一刻,即将退休的我,懵懵懂懂地踏进了写作散文的门槛。一晃四年多,日历翻到2025年7月22日,散文、随笔、小说拢共攒下了整整一百篇。这些文字像一百个脚印,深深浅浅,踩在这段不短也不长的日子里。巧的是,第一百篇《人生是一道数学题》,与启始篇首尾相衔,像一道题的开悟与解答,默默地勾勒出我这段独自跋涉的轨迹。
我写下的文字,源头都在日子里:上班时的零碎感悟,锅碗瓢盆碰出的冷暖,街头巷尾的人情世故……这些琐碎的日常先在心里焐热了,而后落在纸上,便成了“小生活”的微光,“微心情”的颤动。偶尔的一段音乐、不期的一场电影、心怡的一本好书、心仪的一幅字画,也让我赶紧记下波澜;兴头上,还用文言文写点“记”与“赋”,咂一口古味。写着写着,写作不再是退休生活的添头,而是停不下来的心跳,更是我安顿灵魂的港湾。
刚退休那阵子,我像一艘小船跌撞着冲出港口,一头扎进茫茫大海。四十年一贯制的紧绷“啪”地松开,时间从离弦的赛道秒变成天上飘浮的云,没着也没落。手脚不知所向,灵魂无处安放,忒像一个丢了盔甲的兵士,傻傻站在旷野里。幸好还有笔,幸好我握住了笔。写作像一道微光,照进了我灰蒙蒙的心境;重新执笔,让字在纸上流淌,日子立刻有了方向,也有了新的标尺——过去被工作挤得七零八落的生活碎片,如今被文字一片片拾起,细细打磨之后,便有了新意。写作成了重新丈量时间的尺子,也成了重新织造日常的一把穿来复去的梭子。
我写作,不是为了登高望远,颇像是弯下了腰,在生活的最低处捡拾麦穗。菜市场小贩扯着嗓子“冬瓜一块五啦”,隔壁窗台飘来的爆炒辣椒呛香,老槐树下老头老太的闲话……这些曾被匆忙脚步踩过的细碎,如今静下心再看,竟藏着惊人的丰饶,甚至是诗意,还真是最美的风景在路上,在身边。写作让我“坐在生活的前排”,成了自己人生这出戏里的最专注的观众与灵魂的记录者——不只看,还沉浸其中。那些被尘封的旧事,也因文字的擦拭重新泛光。回头望,这一百篇文字,已在时间的河岸上垒起一座小小的灯塔,映照出我平凡生命的一抹清晰而有趣的影子。
不知不觉中,还悄悄架起了一座小桥,把孤岛般的我与广袤无垠的世界连了起来。起初只是把心头的憋屈、欢喜倾倒成肤浅的文字,没想到这些关于“小生活”的絮叨,竟在平台上屡屡激起回响:陌生读者的留言、编辑老师的鼓励、远方朋友的问候,像微光透过窗棂,暖烘烘的。第四篇《我的武汉我的情》参加《人民网》“战疫”征文居然获得了优秀作品奖。这让我深信,最微小的个人体验,只要推心置腹,就能跨过年龄、经历,乃至于时空,在他人的心湖里泛起涟漪。写作不仅是闭门取暖,更是举心为灯,在茫茫人海里照亮同行的人。
四年时光,一百篇文字——早已经不是普通数字叠加,而是一种活法,是对流逝光阴的畅想,是对平凡生活的深情厚意。当第一百篇画上顿号,我才明白:写作已长成生命之树的年轮,是我赖以为生的空气。它给予了退休生活以份量与节奏,让原本平淡的日子在文字淘洗下析出点点金屑,也足以点亮庸常。
是写作,让我于时间急流里稳住心神,于喧嚣尘世之外辟一方静谧的后院。笔尖如针线,把散落的日子缝成了一件暖而韧的衣裳,裹住退休后仍扑腾的心。一百篇文章,是回望的小碑,也是继续前行的号角:生命之河奔涌不息,只要心在感受、笔在流淌,我的故事就远未结束。此刻,窗外的阳光漫过书桌,第一行格子亮堂堂的——第101篇《水饺的归途:一碗漂流的故乡》,纸页徐徐铺开。
| 








 窥视卡
窥视卡 雷达卡
雷达卡



 发表于 2025-8-25 07:49:58
发表于 2025-8-25 07:49:5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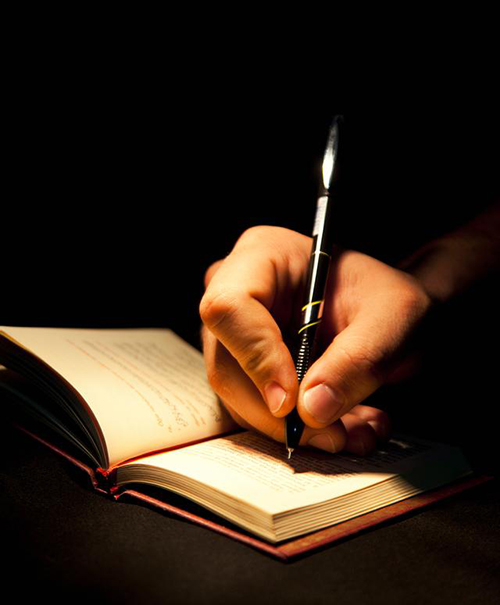
 提升卡
提升卡 置顶卡
置顶卡 沉默卡
沉默卡 喧嚣卡
喧嚣卡 变色卡
变色卡 千斤顶
千斤顶 照妖镜
照妖镜









